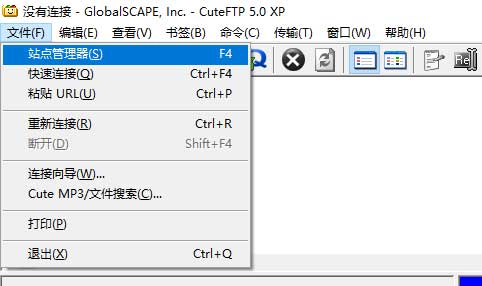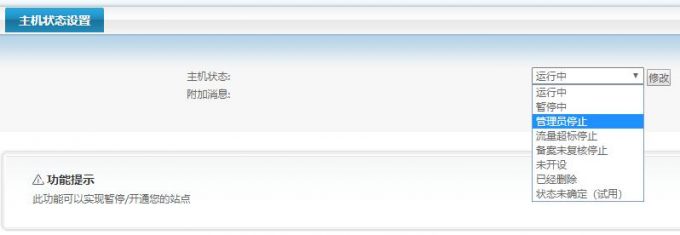六月开什么花?六月开的花的花语你知道么

水生烟
一
沈皓说他要回来的时候,我终于有理由跑去拎回了那条喜欢了很久的孔雀蓝长裙。
那样深湛、明净的蓝,很衬肤色。我在宽大的试衣镜前得意地扬了扬头,虽然付款时仍有一点显而易见的肉疼。可是沈皓要回来了,且第一时间通知的那个人是我,这真有些类似被随机抽取中大奖的错觉。
沈皓在韩国做交换生,一年。他离开的第二天,曾打过一通电话给我。他说,丁晓欧,我书桌里有一本书和一支钢笔,你收起来。
不等我说话,他接着说,丁晓欧,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翻了个白眼。
就因为他的理所当然颐指气使,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只是偶尔会在我新发的状态下面跟一句贱话,丁晓欧又长胖了之类。
二
沈皓留在书桌里的那本书,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第109页,夹着一张白纸裁成的书签,上面是他的笔迹,写了几句诗:你手里拿的那把花/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子/六月开的吗?
语焉不详。当时我并不知晓这两句诗的出处,亦忘记了深究。只是我得承认我怀着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像个急于破译密码的特工般翻看了整本书可以用来写字的空白页码,以及封面封底,却再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来自沈皓的字迹。
哦,109,如果不那么严苛地话,这是我生日的数字组合。当然,我把它理解成一个巧合。
沈皓留下的英雄牌钢笔,黑色,很旧了,他说他用了将近十年。笔尖已经磨成偏锋。后来我用它写笔记时,努力尝试沈皓握笔使力的角度,却因此不小心就让他的模样跳进了我的脑子里。我用力甩头,想要遏止这念头,可是那个人却噙了高傲的笑,以一个屹立不倒的姿势霸占着我有限的思维空间。
三
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百年孤独》,并又一次特工般检查了字里行间,没有发现任何疑似表露心迹的蛛丝马迹。
我试图给沈皓发一则消息,我想说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关系,我不会那么认真地,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地用心读完了这本书。可是我编辑了长长的一行字,然后逐个删除,最后只发送了两个字,沈皓。
他很快回复,干吗,丁晓欧?
没有半点温存。我仿佛看见他瘦高瘦高的个子站在我面前,略低了头,斜睨着眼,语气里是惯有的颐指气使和不耐烦。
然后,快速回他3个字,发错了!
他一下子乐了,说丁晓欧,你对着别人都叫我名字吗?
我的脸红了又红,一颗心像是提在半空似的,有点空荡有点慌张,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欢喜,种种情绪把胸腔填得满满当当。
四
我设想过与沈皓的久别重逢。我穿孔雀蓝的长裙,与他相对而行,渐行渐近。红色方砖铺就的甬路两旁,有细草柔软,在微风中轻颤。
我们对视的目光,会扯出去老远。他会收回那个关于“丁晓欧又长胖了”的恶毒诅咒,那一刻他眼中的丁晓欧盛放成了一朵永不凋零的蓝色鸢尾花。
而事实上,沈皓回来的那天,我根本没穿那条精心准备的裙子。为了掩饰我的紧张和局促,表现出对沈皓回归的不以为意,我套了件已经穿了3天的麻灰色半袖T恤,还故作不羁地把一边袖子挽到了腋下,配一条膝盖大腿处处泛着疲惫褶皱的深蓝棉麻短裤。
沈皓像只珍稀动物一样被大家围在中间,人群叽叽喳喳。人群成了很好的屏障,可当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座位旁坐下,仍旧被沈皓冷不防的一声叫喊,吓得猛地全身弹起。他叫,丁晓欧!
我迅速弹起的速度与姿势,引来一片哄笑。包括,沈皓,他笑得尤其夸张。
我翻了个白眼,扭过脸。窗外蓝天高远,白云片片温柔席卷。而我只是感觉,脸上火烧火燎的热辣,大片红云弥漫。
青春里的心事,不过是欲盖弥彰,因此倒反而成为一种凸显,凸显出真心与在意。相爱的人,定然会懂。

五
宿舍里的姑娘,都有了亲爱的他。夜里手机屏幕闪烁,如同星光散落。在此情境下,我一贯安静的手机猛然发出的一声蜂鸣,迅速引来三颗脑袋的围观。
我讪讪一笑,中奖消息。
是的,是中奖消息。沈皓发来的3个字,睡了吗?
我回,睡了。
等了许久,手机铃声没有再响。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巨大眼袋出现在教室里,过街老鼠般轻手轻脚,因为不敢抬头,自然无从知晓座位上低垂了眼睛的沈皓,破天荒地戴着副黑框眼镜,是不是为了遮掩眼底血丝。
但我清楚看见的是,那天的实验课上,和沈皓同组的女生,花痴般绽放的笑脸。她一定觉得他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烁的全是智慧和博学。
从未有过的醋意翻滚,我一失手,就把塑料量杯玻璃量筒齐齐打翻在地。我慌张地蹲下身捡拾玻璃碎片时,视线里进入了一双黑色帆布鞋的脚。他跟我说,别扎了手。
声音那么近、那么轻,那么,温柔。我刚在心里有了一丝温存蜜意的假想,他接下来的话,却扼杀了我对他的美好想象。
沈皓说,笨呐,丁晓欧,学渣就是这么炼成的。
我蹲在地上,好久没有起身。直到他握了我的胳膊,叫我,小欧?
我站起身,甩开他的胳膊,扭过了脸。我想他并没有看见,我的两滴泪水,刚摔在白色的瓷砖地面,四分五裂。
可是其他人都看见了。于是丁晓欧喜欢沈皓的消息,不胫而走。
六
丁晓欧喜欢沈皓。
我觉得这件事将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班级新闻头条。
为了证明丁晓欧不喜欢沈皓,我主动给对我表示过好感的某位高中同学发了一条看似浪漫、实则矫情而空洞的消息:北湖的荷花开好了,你来看看我吧。
点击确认的时候,我在心底发出了一声哀嚎。因为那一刻我确定,我之所以每次都在沈皓面前表现得那么懦弱差劲,不过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他。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喜欢。
因为认真而较劲、别扭。只是当时的我,不懂,便是懂了,也不肯、不屑于承认。我们都以为,主动的那一个,很丢脸。于是我们各自站在原地,等对方靠近。而事实上,只要有一个人肯迈出脚步,另一个人定然伸出双臂大步相迎。
可惜的是,旷掉了随后整节实验课的我,没能第一时间知晓,沈皓已把我调去了他的组里。
七
北湖的荷花开好了。可是我却不敢约我最想约的那个人,一起去看一看它。
而现在他们都知道了,或许丁晓欧不喜欢沈皓,她有一个外校男友。
丁晓欧不喜欢沈皓。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费力地证明这个,又证明给谁看。
我把那本书还给了沈皓。他接过去的时候抬眼看我。那样直接的、深邃的目光。我可以对旁人编造一个拙劣的谎话,却不能对自己掩饰意乱心慌。我抬起一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我只是害怕,会在他的注视下,一点一点情不自禁地泄露了心底秘密。虽然,那原本便是属于他的啊。
然而我来不及想象,他已顺势握住我的手。
我用眼角余光瞥着旁边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同学,用即将就义赴死的壮烈,笑着跟他说,对不起,我把你的书签弄丢了。
沈皓松开手,说,没关系。
他说,在国外时,我无数遍地背过那首诗。你知道吗,小欧?
我愕然,挑高了眉毛看他时,他便迎着我的目光点头,笑,笑得好温柔。
九
我当然没有真把书签弄丢,我只是把它藏起来了。百度之后,我终于窥见沈皓的别样情绪,它们与诗句一起慢慢浮出水面,渐渐明朗。
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你总有爱我的那一天》:你总有爱我的那一天/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长大/你手里提着的那把花/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子,六月开的吗/如今,我种下满心窝的种子/至少有一两颗,能生根发芽吧……
有生之年,我想我再不会忘记那个傍晚,盛夏夕光红艳。而等我想到这样枯坐不过是辜负,天地间的暮色已然蔓延。像是乘着醺醺醉意,颤抖了手指,我终于大胆地发了条消息给他。我喜欢你。
他的回复很快过来,发错了吧?
没错,就是你。沈皓,我喜欢你。
而他终于不再矫情,回复因此显得很脑残:我也是。
我一下子笑出声来。我知道其实我有那么那么多的话,想要说给他听。
比如我想穿着孔雀蓝长裙的丁晓欧,会是好看的样子。她会束起在等待里已经长及腰背的头发,不再执拗,而是温柔地笑着看他。即使有过那么多酸涩而甜蜜的兜转,而一切还将是初相见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