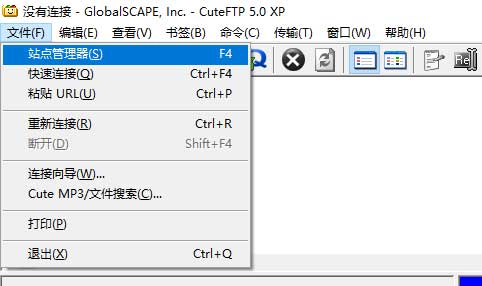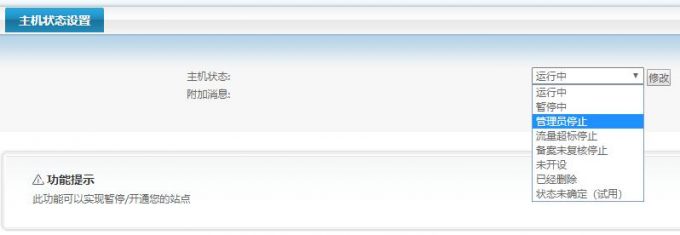河道费税率是多少,河道费税率如何计算!
A车主为其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保险金额为10万元,另投保了三者险,保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某日,A驾车在大桥上行驶中不慎碰撞桥墩后坠入河道。A车主负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经查勘、评估,认为车辆打捞费用过高,无打捞必要,遂推定车辆全损。而河道管理部门认为,车辆的存在危害了航道的通行安全并影响防洪,故根据河道管理的规定组织强制打捞,产生打捞费20万元及河道清理费5万元。
打捞费和河道清理费到底属于三者险的赔偿范围还是车损险的赔偿范围?
河道管理部门和肇事方主张该20万元打捞费和5万元的河道清理费属于保险公司三者险的赔偿范围,而保险公司认为应计入车损险赔偿范围,双方产生争议。对本案的处理形成了两种意见:意见一认为,打捞费性质为施救费用,应在车损险范围内处理,河道清理费属第三者损失;意见二认为,打捞的目的是为了航道的通行安全和顺利泄洪,打捞费和河道清理费均是第三者产生的损失,均应由保险公司在三者险限额内赔偿。

立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界定,解决案件争议
1.车损险和三者险保险责任范围的区分。
在一般情形下,车损险和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是泾渭分明的。车损险即机动车损失保险,是财产损失保险的一种。财产损失保险是以各种有形的物质财产、相关的利益以及其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对机动车损失保险中保险责任范围的界定,其承保范围是因特定原因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条款》还明确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施救费用数额在被保险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及《河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河道内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如果影响航行安全或影响防洪,职能管理部门可以强制打捞。因A负事故全部责任,本案中20万元打捞费用及5万元河道清理费属于A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这点自无异议。但界定属于A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之后,认定该赔偿责任属于车损险还是三者险的理赔范围则对当事人权益影响很大。如果属于车损险理赔范围,则需要审查上述25万元费用是否属于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且即使属于,保险人承担的该费用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即10万元。而如果属于三者险理赔范围,因保险限额足够,保险人对该25万元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打捞费、河道清理费的性质及解释。
笔者认为,就本案的处理应当结合费用的性质和目的进行判断。车损险赔偿的施救费用系针对的机动车的价值本身,其产生的目的在于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通过施救费用的发生,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得以降低,被保险人的损失得到了控制,进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也得到了控制。如机动车倾覆于路边,通过吊运,机动车得以移动至路面,为下一步的修理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吊运这一施救行为,机动车无法回复原状,机动车的原有价值也不能发挥。可见,施救对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来说可以取得共赢的效果,这也符合物尽其用原则的要求。通常而言,施救费与保险标的的损失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当然,即便进行施救花费了费用,但并未奏效,保险标的仍然全损,保险人对施救费用仍予负责,只要这些费用是必要的、合理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施救费由保险人在被保险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是因为该费用附着于机动车。与此相对应,三者险负担的损失是因被保险机动车的使用造成的第三者的损失。施救费有时也是第三者支出的,但这种情形下第三者之所以施救要不是因被保险人的请求,要不是出于维护保险标的的本身。而被保险人请求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持被保险机动车的本身价值。相比之下,第三者的损失虽然是由于被保险机动车造成的,但第三者的损失与保险标的本身的损失截然不同。《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第三者损失的存在与否以及损失的大小均与保险标的的本身损失没有必然的关联。对维护保险标的产生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保险人应当在保险金额的数额内承担。对第三者的损失,则需考虑被保险人是否应当赔偿及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由被保险人赔偿的第三者的损失才能计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
本案中车辆由于打捞费用过高,单纯因为恢复车辆的价值已无打捞的必要。20万元打捞费用及5万元河道清理费是基于维护航道的通行安全及防洪的考虑。A造成的交通事故导致了航道的通行安全受影响,产生了防洪的隐患,由此带来的清除隐患的费用都是因事故造成的第三者的损失。A应当对这些费用承担赔偿责任,故这些费用应当计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当然,如果因为打捞,车辆得到了修理,机动车的价值同时得到了维护,打捞费的本身也产生了减少机动车损失的效果,也可酌情部分计入车损险的赔偿范围。毕竟,此时保险人原本要对机动车的全损10万元进行赔偿,现在因打捞其赔偿车损的金额减少,让其在车损险赔偿范围内适当负担打捞费用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3.对保险责任范围的解释应慎用不利解释规则。
在格式合同中,由于合同提供者的优势地位,相对的一方只能选择接受或者离开两种结果,而没有协商的能力。为了打破这种附合化的状况,合同法规定了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保险法》也作了相应规定。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适用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适用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但不利解释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滥用的现象。许多法院割裂了一般合同解释与保险合同解释的共性和关联,将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障视为合同解释的终极目标与判断结果正当性的唯一标准。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保险责任范围是一个险种的基础,是对价均衡原则的重要体现。任何险险种均存在一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之中保险人承担的范围都不是无限的。对其的解释应当立足于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法的法理、惯例等,不能对保险责任范围随意进行解释。其次,应当明确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顺序。《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如果依照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能够确定条款的具体含义,并无不利解释规则的出场必要。再次,保险合同的条款的“歧义”不等同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分歧”。保险条款的体现真实含义是什么,应当以理性第三人的标准合理界定。即歧义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构造。不能因为原、被告双方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不同,即当然认为条款存在歧义。本案中的车损险和三者险各有各的保险责任范围,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认为三者险限额高,就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第三者而当然地将费用往该险种中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