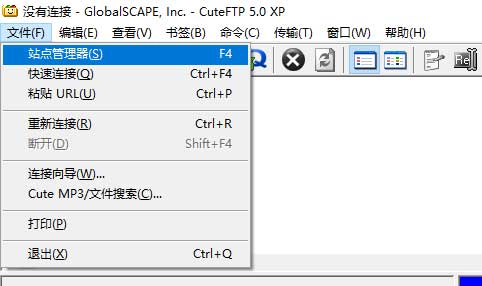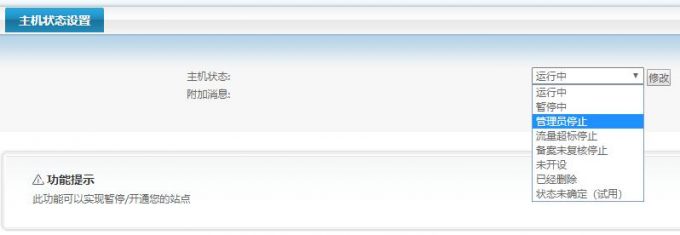新医改评论(最新医改内容、最新政策)
“年前看个小病,请了十次假,一半年终奖泡汤了,医院看病何时不用跑断腿?”今年初,一名知乎大V分享了一段看病经历,激起了2019年第一场关于“就医难”的讨论。
这名知乎网友的遭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他感到目眩,恶心、呕吐,折腾了整整一夜。此后一个月,他去了8次医院,先后到三个科室就诊,做了两次磁共振检查,最后在耳鼻喉科诊断为耳石症(良性位置性眩晕)。随后,诊断医生在检查床上做了10分钟手法复位,病症就神奇消失了。
由于多次请假,这名网友的工作大部分被其它同事承担了,同事们诸多抱怨,他本人的年终奖也只能减半。虽然结局并不算最糟糕,但看似折腾的就医经历引发诸多关于看病难的话题“共振”:
有人回忆起配药的麻烦;有人无奈大医院人满为患,排队一上午,看病三分钟;还有人说现在医院科室分的越来越细,看个病都不知道挂什么科。不过也有人说,一个月解决了问题,医疗系统的效率已经很高了。
“看病难、看病贵”,中国普通百姓习惯了用这六个字概括他们对医疗保障的集体焦虑。十多年前,正是意识到这种集体焦虑,新一轮医改于2009年正式启动。十年过去了,新医改的下一个十年往哪里走?
至少眼下,“看病难、看病贵”这张考卷还一直摆在中国领导层的案头,解决这道难题仍然是医改下半程的终极使命与核心任务。
多元的“看病难、看病贵”
一年的求医经历过后,河南人卢瑶对“看病难、看病贵”有了更切身的感受。2018年2月,卢瑶年幼的女儿查出了白血病。为了给女儿看病,卢瑶带女儿从河南南阳到邻近北京的河北三河,这里有一家擅长血液疾病的医院。对这个农村家庭而言,女儿的病是一场灾难。
女儿发病快满一年,所花医疗费用总计已超80万,医保报销比例达到60%,仍有将近40万需要自付。卢瑶和丈夫两口子存折里的积蓄已然荡然一空,他们借了不少钱。只要女儿的病没治好,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一点点地把这个家,拖入贫穷的深渊。
卢瑶的丈夫对治愈女儿失去了信心。或许是考虑到还有个小儿子需要照顾,他铁心不愿再坚持,甚至当着女儿的面,对妻子说,“不可能为了她,下半辈子过上欠钱的日子”。小姑娘一脸无辜,半躺在病床上,看着她最亲近的人为此争吵甚至出手。
距离卢瑶和她女儿所在病房大约几十公里之外,北京城里的何大爷最近刚在京城一家三甲大医院里做完了一场心脏手术。在心脏内科监护室(CCU)里住了好几天,何大爷想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何大爷有个三十岁的独生女何梅,刚辞了工作,正好有空陪他一起看病。跟卢瑶一样,何梅也觉得看病“挺难的”。“虽然北京是医疗资源的高地,但想要挂上专家号也不容易。”
何梅带何大爷去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医生。有几次,她直接自己拿着病历去挂号找医生看,“说的都不太一样”。何梅觉得,看病难在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怎么样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好的”。
何梅知道,人的身体与疾病是非常复杂的,当医生看到的只有检验结果时,可能做出的判断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她总是想试着像“货比三家”一样多问问。
对于从农村来的卢瑶来说,这是另一种她能够理解,但无法体会的“看病难”。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叹的往往不是医疗服务的便利可及,而是医疗服务的质量。当他们好不容易挂上号,排了队,只跟医生聊了五分钟,然后又要去排队缴费。这三长一短(挂号、候诊、收费队伍长,看病时间短)就是他们眼中的最大的“看病难”。
南都记者曾听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老年人讲起自己往日跑大医院的体验。74岁的老唐,患有房颤、高血压、肺气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等多种慢性病,跑医院在他看来是自己的“日常功课”。
为了挂上海中山医院专家号,老唐4点起床,5点打车到医院。和其他通宵排队的人比,他还是来晚了,只能在号贩子处花了400元买了一个专家号。看完病,“每次回家以后,总是感觉很累很累,心里总是不高兴,每个月总是要这样折腾几次”。
正因为此,何大爷一点也不喜欢去大医院人挤人。在这次心脏手术之前,何大爷很久没有去过医院,患糖尿病十年,他一直在服用一种降糖药,但是从不监测自己的血糖,不了解血糖控制情况,他觉得吃了药就会有效;而在日常生活中,何大爷一直没有戒酒,退休至今五年,没有做过一次体检。
一年前,何大爷曾发生过一次肺部感染。当时医生在检查时发现问题,提醒他除了肺部感染,肾脏和心脏都出现一些问题。但何大爷没有重视,他以为,“肾脏和心脏的问题都是肺部感染带来的,这次把肺部感染治好了就没有问题”。
何大爷缺乏自我健康管理的后果,就是他终于在2018年被推进了心内科的手术室。
对独生女何梅来说,陪父母看病让她身心俱疲。“他们很糊涂,搞不清楚状况,对医生说的、要求做的,没有意识也缺乏判断”,女儿说。
十年前,新医改承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健康的灵魂都是相似的,受苦的皮肉却各有各的“看病难”。
现在的“看病难”也和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40年前,中国人的看病难更多是因为资源供给短缺造成的住院难、手术难;到如今,供给侧改革依然相对滞后,地区间差异较40年前拉的更大,不均衡问题更突显;与此同时,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却在飞涨。
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胡强强这样描述:现在中国面对的“看病难”问题是“供需侧双向约束的结果”。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在出版的《中国发展评论》上发表了一篇160多页的报告,题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提出的结论丝毫不留情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彼时的中国,在供给侧上,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追求公益与追求经济之间出现失衡。
而在需求侧,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都不具有强制性,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保,看病基本上靠自费。
2003年,原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呈现,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而在中国卫生总支出费用中,由个人支出的部分占到50%以上。还有30%多来自社会,政府支出只有20%不到。这样的数据投射到大多数中国居民的生活中,就是“看病难、看病贵”。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方面做了绩效评估。在其中的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188位,倒数第四。
在媒体对这篇报告关注报道之后,一时间,“中国医改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搅动全国上下,但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序幕,人称“新医改”。
经过三年的政策讨论,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启动了“新医改”,而改革方案也承诺:“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十年“新医改”的总体评价又是如何,仍有待评估和审视。
但一些在2005年国务院智库报告中被提及的医改举措已经实施。比如,在最震撼的医药分开改革中,公立医院15%的药品加成全部取消;虽然医疗保险待遇保障还较低,但覆盖率达到了95%;在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的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排名中,2016年的中国升至全球第48位。
为解决看病贵的问题,2018年,越来越多的抗癌药得以更快速度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一些通过谈判降价进入了医保;近三十年来,卫生支出中的个人负担占比也降到了30%以内,达到28%;分级诊疗成为医改五大任务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医改政策参与者和卫生健康部门官员近期密集表态,强调医改的核心命题,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2018年末在北京一场论坛上说,医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主要聚焦在3个方面——第一,解决看病难问题;第二,缓解看病贵问题;第三,解决医疗卫生系统或者机构的管理问题。
在广东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监察专员姚建红亦表示,医改下一步,仍要继续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1月10日,国家卫健委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了2019年的10项卫生健康重点工作。其中,其中5项工作直接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相关——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三医”联动改革、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十年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有哪些新路径?
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医改面对的命题依然没有变,但实施路径也许稍有改变。
解决看病难,梁万年坦言,在优质资源稀缺的状况下,首先要谋求资源的增量,可以通过发展社会力量办医增加资源供给。
就在最近,国家发改委等九个部门发布一份重磅通知,要求各省“制定社会办医准入跨部门审批流程和事项清单,取消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前置条件和申请材料,进一步为社会办医松绑。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效率和效益,进行合理的分工、定位,使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真正回归各自的功能定位,同时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实现良性运行。”梁万年说。
“在破解‘看病难’问题方面,主要依靠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也说,具体做法包括推进医联体建设、加强县医院建设以及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胡强强看来,“医联体建设”是解决看病难问题重要的实施路径,也是为未来构建整合型医疗服务模式打下制度基础。目前,官方对医联体建设的形成十六个字的总体思路——规划发展、分区包段、防治结合、行业监管。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卫学院院长刘远立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几次强调,“专业和组织的碎片化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一站式、连续式、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不匹配。未来中国医疗发展最核心的方向一定是走向整合医疗。”
新医改第一个十年,“整合”的任务开了头,却没能很好完成,甚至出现一些宏观方向的偏差。最大的问题是基层的持续弱化一度还在加速,有统计显示,2002至2013年的10年间,基层卫生机构数量小幅下降了6%;而二级医院数量上升29%,三级医院数量上升了82%。
这段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基层医疗机构逐渐被边缘化。2010-2014年五年里,医院诊疗人次数占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比重从34.9%上升到39.1%,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比重由61.9%降至57.4%。
2015年以来,政府陆续推出了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文件,试图重返“强基层”的目标。
2019的医改目标提出,将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制度,从医疗服务体系、资源布局和功能调整完善入手,有效盘活存量,引导优质资源下沉,引导患者有序就医。
梁万年说,分级诊疗将牢牢抓住“医联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远程医疗三个抓手”。他认为,构建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关键还是要把医疗机构回归到本来的定位,进行有效协同,结束当前无序竞争。”
对于农村地区的医改,县医院的能力建设成为牛鼻子。“提升县医院的能力是实现农民看病不出县的关键。”胡强强说,按照新一轮的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要求,供给侧医改要重点发展县医院在肿瘤、心脑血管、感染性疾病等诊疗能力,力争农民90%的疾病在县医院得到解决。
对农民而言,这既是解决看病难,也是解决看病贵。卢瑶因为异地就医,报销无比麻烦,她只能隔一段时间回家乡报销,这样才能差出下一笔治疗费用。
另一方面,县医院也将通过更大范围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以及“远程医疗”业务,来实现与上下医疗机构之间的“整合”。胡强强介绍,到2020年,远程医疗要覆盖到全部贫困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并向村卫生室延伸。
上海的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8年,上海家庭医生“1+1+1”医疗机构组合(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二级医院+一家三级医院)签约居民666万人,30%的上海常住居民已经有了家庭医生。老唐再不用大清早去大医院排队挂号配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医护团队负责他的疾病管理。
南都记者注意到,“编制规划,积极探索建设整合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已经写入2019年卫生健康工作计划。老年医疗护理体系或成为整合医疗模式的试验田。
除了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外部整合与协同,医疗机构内部的整合也是未来医改方向。刘远立认为,同一个医疗机构内不同的专科之间的跨学科整合,这种跨学科的重要性和强大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肿瘤复杂疾病群,内整合不光是多学科的整合,还包括生理治疗、心理治疗、身心整合以及临终关怀等。
一位国家卫健委官员曾说,医学专科划分越来越细,学科各管一段的问题在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疾病特别突出。比如心内科和心外科,心内科的医生认为患者可以放支架治疗,但却给心外科医生动了刀;心外科的医生也觉得明明是需要手术的病人却在心内科治疗。
而在肿瘤治疗领域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患者采用什么样治疗的手段取决于挂了哪个科室医生的号。“跳出专科看疾病,真正站在病人角度考虑问题太少了”。